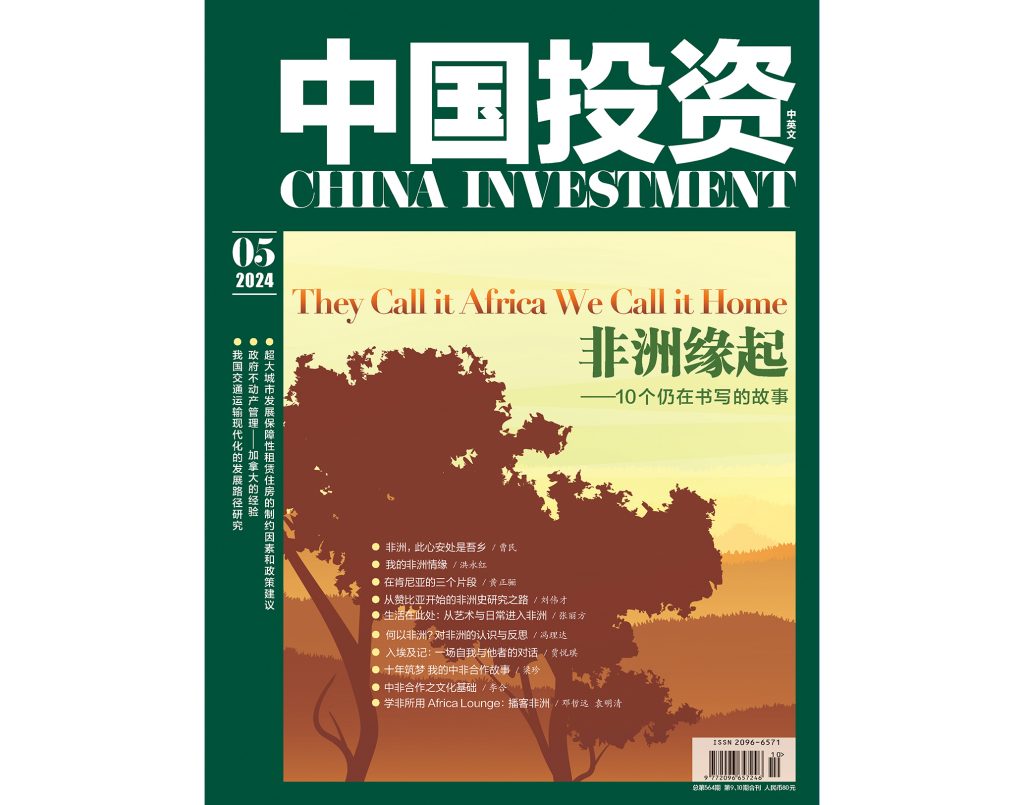
5月号封面故事
非洲缘起
——10个仍在书写的故事
● 我的非洲情缘 /洪永红
● 在肯尼亚的三个片段 / 刘伟才
● 生活在此处:从艺术与日常进入非洲 / 张丽方
● 何以非洲?对非洲的认识与反思 / 冯理达
● 入埃及记:一场自我与他者的对话 / 贾悦琪
● 十年筑梦 我的中非合作故事 / 梁珍
● 中非合作之文化基础 / 李合
● 学非所用Africa Lounge:播客非洲 / 邓哲远 袁明清

文|刘伟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图片提供|刘伟才
导读
●初识非洲
●走进赞比亚
● 在赞比亚大学的学习与阅读
●结语

⬆ 2008年在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
2004年开始读研时,我对非洲基本没有认识——老实说,也基本没有兴趣。
因为在本科时玩过“罗马复兴”和“帝国时代”之类的游戏,所以当时其实对古代中世纪史更感兴趣,再就是觉得近现代大国兴衰史也挺有意思,总觉得波澜壮阔或者波诡云谲才是历史,或者至少要有一些可让人废书而叹、让人荡气回肠的人和事吧!而当时所知的非洲,也就是那些自己现在看起来属于标签化的认识如“黑人”“沙漠”“炎热”“饥荒”“政变”“战乱”之类;当时了解的非洲历史,好像也就是一些连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都缺失的东西,极度平淡,感觉就算不是“无历史”,那也是没什么意思的历史。
也就是在这时,中非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虽然当时对此并没有多少认识,但这种变化却还是影响到了我。

⬆ 在赞比亚大学住地(Marshland)的学习桌
初识非洲
对非政策文件》发布。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属于冷门或者一度在政治层面比较热但实际上一直很冷的非洲史研究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当时的现实是,从事非洲史研究的机构和人员非常非常少。我的导师长期从事非洲史研究,也不断地在一些场合呼吁要加强非洲史研究,但真正的转机却似乎直到此时才出现。一些人希望上面重视非洲研究并给予实质性具体支持的呼吁得到了回应,在导师的支持下,我获得了赴赞比亚大学学习的机会。
办理相关事宜的过程并不顺利——但这个过程却是我认识非洲的开始。简单来说,就是过程非常慢,慢到以我当时的认知完全无法想象。学校相关部门的人员多次抱怨说,一个邮件过去总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回了也是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本来认为最多一两个月就应该能解决的事,可能光沟通明白就需要大半年。实际上,直到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事情也没有眉目。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是连着继续读博,那这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在等待或者说不再有心等待的过程中,我按部就班,先要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在选题和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可以选的题目倒是不少,资料却是奇缺。不说一手文献吧,就二手的著作、论文等,很多主题也都是空白,或者只有一星半点的介绍类的东西。按说,总归先要对非洲整体或者具体区域、国家的情况有一个大致了解,再对相关领域有一些整体认识,但当时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八卷本《非洲通史》和我们自己的三卷本《非洲通史》外,就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一批大字本的翻译过来的非洲国家历史方面的著作,细致个案方面的研究极少极少,一些文献线索以我当时的水平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那个时候,网络数据资源还不像现在这么丰富,网络本身其实也算不上发达。
不过,正是这种情况,却让我有了一定的深入探索的兴趣。我当时的疑惑是,怎么这么多问题都没有人关注和研究呢?怎么这么多问题搞不清楚还找不到资料呢?我当时就有了想法,想把一些问题搞清楚——这可以说是我后来从事非洲史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我不是很赞同一些人所说的要热爱非洲研究事业、对非洲有情怀或者感情之类,我就是单纯想把一些问题搞清楚。
带着想把一些问题搞清楚的念头,我以一向以来的好像不太好但始终没办法改的读书习惯,囫囵吞枣地看了一些当时比较容易找到的与非洲历史相关的书籍。数量不算少,但印象特别深的并不多,好像就是零零碎碎地往脑子里塞了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对一些名字和名词有了一个记忆,但对一些主题的疑惑却越来越深了,就是觉得很多关于非洲历史的东西都不清不楚,一些叙述也似乎难以理解,比如古代的一些内容,明明都没有说清楚,但却一定要强调其具有较高地位且发挥了突出作用;比如殖民时期的一些内容,明明具体的定量情况是这样,但定性却一定要那样;比如现当代的一些内容,明明说了非洲的很多问题,但问题的原因归结却总是在非洲之外。还有一些算是宏观层面的疑惑,比如为什么整整一个种族都与奴隶、种族主义相联系,为什么几乎整个大陆都沦为殖民地之类。
本来是想把一些问题搞清楚,结果疑惑却越来越多。

⬆ 在赞比亚期间从事兼职工作处的菜地

⬆ 在赞比亚期间从事兼职工作处的牛群

⬆ 在赞比亚期间从事兼职工作处的桥梁
走进赞比亚
2007年开始读博,一年多前就开始说的去赞比亚的事,竟一度没了音信。然后又过了大半年,事情才真正落定,但此时的心情已是犹豫抵触居多。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在2008年6月踏上了前往赞比亚之路。
在从肯尼斯·卡翁达国际机场通往赞比亚大学的大东路上,我带着有些新奇又有些失望的情绪,第一次见识了那具有非洲特色的景象和人物:稀树草原、平顶树、星点分布的铁皮顶或者草顶的房屋、尘土飞扬的路、头顶东西的妇女、三五成群在路边不知有事还是没事的男人、挺着肚子赤着脚的非洲儿童……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识非洲人的行政效率:赞比亚大学的学生证,花了三四个月才领到;每个月100美元的生活补助,过了四五个月才领到;按要求所需的学习许可,则从头到尾都没有领到——为此,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移民局续签证,然后不得不见证移民局工作人员的动作缓慢。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一个工作人员拿着一串钥匙开一个柜,一把一把地试,气定神闲,几分钟就这样过去,要不是试到约三分之一试到了,就不知道还要多久。当然,所有这一切,后来慢慢也适应了,慢慢还觉得理所当然了,当发现有人抱怨这种事时,还会觉得抱怨者不理解非洲和非洲人——不知道这算不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然后是见识了赞比亚大学的老师罢课。就是说,快要考试了,却忽然发现校园安静了不少,有点诡异,正在莫名其妙时,有人告诉我说老师们罢课了,很多学生也回去了,考试时间待定。当时就比较懵,毕竟那时见识实在太少,就觉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不是应该勒紧腰带、顾全大局吗?但好吧,毕竟暂时不用考试,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然后有些糊里糊涂地过了一个月的样子,在住地的院子遇到一位同班的非洲同学,他过来跟我说,老师在找你们呢!我当时想,啥意思?他就说,复课了,要去上课了,你看这段都找不到你们。确实,当时住地没有网络,手机号也没留给学校,压根儿就不知道啥时就复课了。
最大的见识是来自赞比亚北方城镇基特韦的一个中资农场,我在那做了大概一个月的翻译,每天与农场上的非洲工人打交道,第一次真正比较深入地接触了非洲的基层社会。那些工人中,有善于管理非洲工人、在中资老板面前“情商”很高、有两个老婆的工头维克多,也算是十里八乡的“成功人士”;有会开车并掌握一定修车技术但却常常只能干农活因而有些郁郁不得志的“贾斯汀先生”,因为老板有一次安排他拔草而愤然离去;有每月骑自行车去卢本巴希给妻子的摊子进货、每天按时抽两支烟的自律的因诺森,虽然有卡车驾驶证,但在被安排拔草时也笑着接受;有英语也说不好的放牛工芬达,因为被提为放牛主管而“感恩戴德”;有农场上的非洲小孩,好像每天都不上学的样子,有时在林子里找果子,有时捞鱼,有时结伴到有些远的有小卖部的村子里去。
还有时不时来农场进鱼、卷心菜、洋葱等去附近村庄贩卖的妇女,有次因为看上了地里切下的萝卜缨子而老板不同意她们拾走而颇为不满,她们不知道中国人会拿它们做咸菜;有来给农场的牛看病的非洲兽医,对于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解决方案:打针;有时也会有人来“找麻烦”,拿着工会的什么文件,交涉不知什么时候落下的工资纠纷。此外,农场周边还有一些白人的农场,一家养奶牛,一家养鱼,一家有干草卖,还有远一点的一家养鸡养羊。养鸡养羊的这一家,还提供住宿和农场旅游服务,有专门的经理人管理,比较成熟、规范。这家农场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份贴在办公室门上的公告,告诉那些对什么工资、待遇有异议的工人直接去找农场主的律师,完全不是中资公司那种常常要靠老板或管理人员出来吵的套路。
在非洲见识过非洲之后,就会更深切地明白,研究非洲,就一定要去非洲、在非洲。

⬆ 赞比亚大学历史系所在楼宇

⬆ 卢萨卡大东路,左方建筑群为作者在赞比亚大学期间住地

⬆ 雨季来临时的赞比亚大学校园
在赞比亚大学的学习与阅读
当然,主要的时间仍是在赞比亚大学,学习仍是主要任务。
赞比亚大学历史系当时给我们安排了四位导师。其中一位是姆维尔瓦·姆桑巴奇玛(Mwelwa Musambachime),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受教于让·范西纳(Jan Vansina),曾任赞比亚驻联合国代表,是历史系少有的几位教授之一。这位教授给我们讲非洲经济史,在讲到非洲本土经济中的一些事物时,总是喜欢说 “veli veli important”(非常非常重要),有个洛兹族(Lozi)的学生课余就喜欢拿腔拿调地学这句。在上过几次课之后,我开始对非洲本土经济有一些算是“入门”的认识。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始认识到要用非洲的眼光和标准来看非洲经济。姆桑巴奇玛说的那些“veli veli important”的东西,其实就是锄头、牛、羊、高粱、小米、葫芦、南瓜之类,顶多再加上黄金、象牙;然后我在卢萨卡所见的市场与贸易,其实往往就是一块布铺在地上简单摆几样商品的摊子、头顶篮筐的女商贩和一手拎一只鸡或者一手提一件衬衫的男商贩,那些有个一两平米门面卖手机卡或者充电器的,都可算小企业家了。所以,不能以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待和衡量非洲国家的经济生活。
尽管当时赞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显然是很多年没有实质性更新,但对于我来说,那仍是一座宝库。很多书是当时国内难以找到的,还有很多赞比亚本国和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的书籍和档案材料,尤其是关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材料。最令人关注的是一个地下仓库,里面堆满了保存口述资料的磁带。记得当时看到那些堆放得有些像垃圾堆的磁带时,有一种有朝一日要让这些资料得到利用的雄心,但更多的是怅然:那些磁带显然已经堆放很久了,以赞比亚发展的情况,如果没有外部世界的兴趣和关注,它们恐怕很难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也许好多早已毁坏。时至今日,我仍时不时想起那些磁带,但似乎也没有能力去做些什么。
不过,赞比亚大学图书馆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初次进入后的身体不适。犹记第一次进图书馆,不久后就觉得胸闷气短,头冒虚汗,当时心想完了,才来几天就生病了吗?于是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图书馆,整个人立马就神清气爽了。所以,不是生病,是因为不适应图书馆里面的环境?后来我又试了几次,基本证实了这种推测。我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图书馆建筑和里面书架桌椅的年久老旧是一个原因,各种书的年久老旧是一个原因,日常维护管理也有很大关系。后来还去过一些非洲国家大学的图书馆,其中博茨瓦纳大学图书馆最为宽敞明亮,书比较新,整理维护也比较好。想来,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最重要大学的图书馆的状况,也许就是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
但不管怎样,图书馆仍是主要阵地。我在赞比亚图书馆读的东西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前身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相关的资料,这成为我后来博士论文的基础;一部分与津巴布韦相关,主要是罗得西亚时代出的两套早期白人殖民者记录的重印丛书,这可以说是我最近几年关注津巴布韦和19世纪欧洲人非洲旅行记录的一个有些遥远的前奏;一部分是以伊丽莎白·科尔森(Elizabeth Colson)为代表的罗得斯-利文斯顿研究所(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学者的人类学著作,这成为我后来认识和理解非洲史的一个重要框架和路径。
尤其是伊丽莎白·科尔森这位女人类学家关于通加人的研究,让我初步认识了人类学及其方法,那种从看起来不起眼的日常细节演绎和归纳深层主题的路数,让当时对人类学基本没认识的我深受震动,并且当时也发现自己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观察和把握细节并进行上升的天分,于是就立意揣摩学习。还有一点是,伊丽莎白·科尔森关注了通加人约60年,这也让我认识到了研究是一条长路,也应该是一条长路。


⬆ 2008年卢萨卡工艺品市场一角

⬆ 2008年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表演的赞比亚乐队
结语
2009年从赞比亚回来后,我算是真正走上了非洲史研究之路。
回想起来,我在对非洲史研究并没有多少兴趣的情况下站到了非洲史研究领域的门前,又在对非洲没有多少向往和期待的情况下踏上了非洲的土地,然后在之后的十余年里却一直持续并且也可称努力地从事非洲史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似乎有些说不通。如果要说得通的话,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就是在赞比亚的那段并不算长的岁月,那是一段改变我固有认知并让我接受从未想过去接受的新知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