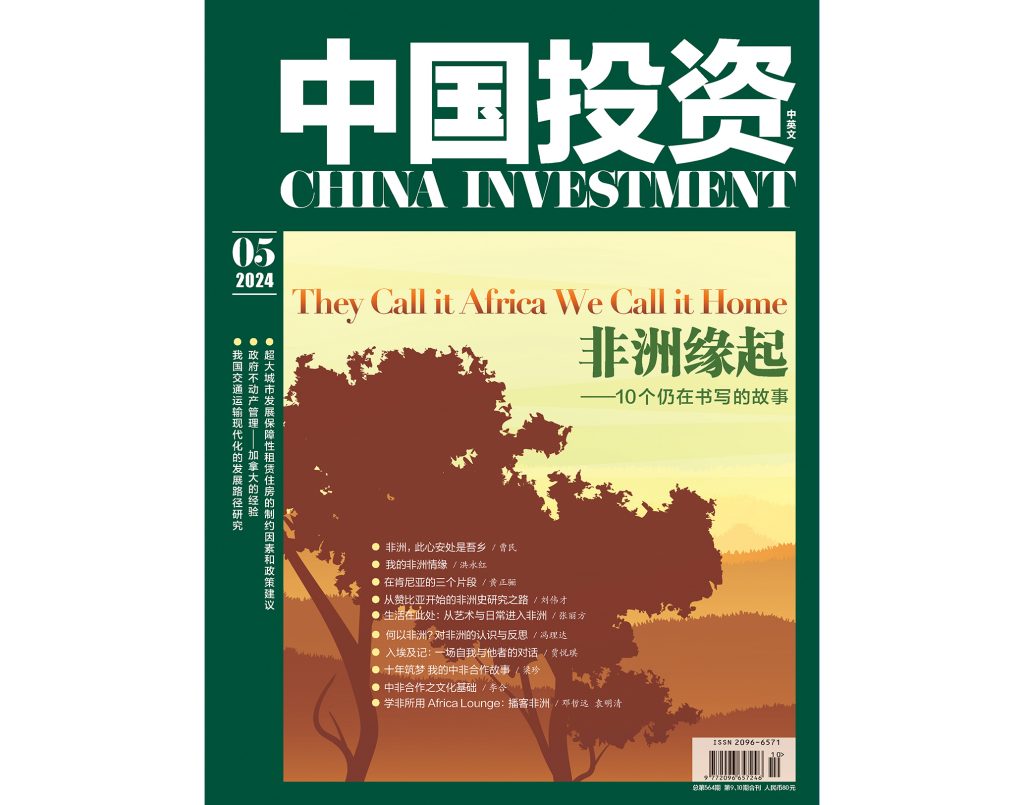
5月号封面故事
非洲缘起
——10个仍在书写的故事
● 我的非洲情缘 /洪永红
● 在肯尼亚的三个片段 / 刘伟才
● 生活在此处:从艺术与日常进入非洲 / 张丽方
● 何以非洲?对非洲的认识与反思 / 冯理达
● 入埃及记:一场自我与他者的对话 / 贾悦琪
● 十年筑梦 我的中非合作故事 / 梁珍
● 中非合作之文化基础 / 李合
● 学非所用Africa Lounge:播客非洲 / 邓哲远 袁明清

文|黄正骊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英国城市研究基金会国际访问学者 图片提供|黄正骊 自然 廖亮 齐林
导读
●西奥港的足球教练
● 班尼迪克和劳力士
●老城里的康教授

⬆ 作者(左三女士)与肯尼亚MCEDO北京学校建成后所有工人的合影
西奥港的足球教练
2011年12月的一天,我在肯尼亚-乌干达边境一个叫西奥港(Sio Port)的小镇参加一场肯尼亚少年足球联赛的半决赛和总决赛。五个月之前,我第一次来到非洲,前往肯尼亚内罗毕的联合国人居署实习。在此之前我对非洲几乎一无所知,而五个月之间我参加了多个贫民窟改造项目,还被派往肯尼亚西部的基苏木市驻地调研。此时的我尽管对非洲城市依旧很无知,但我在此间给博士导师的邮件中写道:虽然尚无法理性总结我在非洲的经历,但此间工作终于让我感觉到城市研究的意义。
为了节约时间,在这个叫西奥港的地方,肯尼亚的少年们决定把半决赛和决赛一起搞了。这意味着所有的人在这里将度过漫长的一天,运动员们将消耗大量体力,而我也在当日的5点多就从基苏木起身,在大巴上颠簸三个小时,来到烈日下的西奥港足球场。从基苏木到西奥港这一区域实在不算什么发达地区,道路坑坑洼洼,大巴在避让坑洞的缓行中偶尔加速,颠簸让本想在车上补觉的我因脑袋频频磕上车窗玻璃而眩晕,晨光里的草原乡村风光、车旁好奇并行的老鹰却也让人心情愉快。因为我参与募集了这场决赛的一部分奖品,又离决赛地点很近,主办方热情地邀请我作为嘉宾观摩这场比赛。
临近赤道的西奥港足球场一半是草一半是沙,比赛从中午11点进行到下午5点,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大部分少年是光脚比赛,半决赛所有的制服都是向年龄较大的球员借来的,大多腋下已经开线。我看着这些14岁光景的少年,纤细的四肢和躯体在太阳底下熠熠生辉,动作协调而灵动,心里好生钦佩。运动员们大多不住在西奥港,一大半的孩子住在5公里甚至10公里开外的地方,一大清早就翻山越岭,徒步几个小时走到这里。半决赛结束后,得胜的队伍稍作休息就进入了决赛。我问他们为什么踢足球,一个孩子想想说,足球好像是我小时候接触到唯一的运动;爸爸用绳子把破布一捆,我们就在茅草地上踢起来了。
球赛的间隙我正和几个少年运动员聊着天,一个高大健壮却愁眉苦脸的教练向我走了过来。在正午的太阳中我看到了他紧锁的眉间释放出的压迫感,让我后脑勺一紧。这样的愁苦神情对于在肯尼亚贫穷地区工作多日的我已经不再陌生。我作为现场唯一的外国人,经常被礼貌地伸手要钱。起初我会倾囊相授,但次数多了就让人无所适从。果不其然,教练走来后压低了声音,用他毕生最为客气的英语对我柔声说:“女士你好,我想以友好的态度请求你伸出援手,给予我们一些财务的赞助;我们学校的球场,球门是木头支的,很容易就折了,木刺也容易伤人;我想把它们换成铁的,让孩子们更安全地运动。”他话音未落我就抢答道:“我自己并没有钱,但我会把少年们的努力记录下来,然后我的朋友会看见,朋友的朋友也会看见。好好踢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说完我就走开了。我心想,许多穷人活得有自信和自尊,会利用有限的资源过最适宜的生活而不要求别人的怜悯;但也有一些人处处依赖接济,就是这些人让这个世界误以为穷人只有受到接济才能存活。所以我看到这位苦情的中年男教练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茫然间我回头望了一眼,只见这苦情男摇身一变,正怒目圆瞪训斥刚才没有好好踢球的两个小孩,把他们骂的低头不语。突然我好像被针扎了一下。一个在孩子们面前素来威严无比的教练,一个肩膀宽阔胸脯厚实的中年男人,想必曾经对足球一样充满希冀而眼神里的激情已经被洗刷了干净,却为了这群对足球这一唯一的体育运动仍旧怀有希望的少年,放下自己的尊严和威望低声下气地对一个连足球也不懂的外国人乞求帮助,这举动本身需要多少勇气和力量。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感到自己放下了自己的顽固,学会了不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我感到有一扇门为我打开,从这天开始我允许新的逻辑、视角和观点自由地进入我的脑子,我对非洲的了解也才真正开始。

⬆ 西奥港(Sio-Port)的少年足球赛

⬆ 球赛中少年们看着奖杯

⬆ 球赛中少年们看着奖杯
班尼迪克和劳力士
2014年4月-9月,我在肯尼亚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谷(Mathare Valley)建造一个学校,叫MCEDO北京学校。学校的南面有一个小山坡,在工程进入正常施工之后,我有时会坐在坡顶上观察工程进度。8月的一天,项目终于进入正式施工,我坐在小山坡顶上回忆三个月以来的折腾,一边自嘲为何会为这么小的一个项目吃这么多苦。
学校位于贫民窟内部,建筑的预算、操作空间、工程时间都控制得非常有限,因此采用了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朱竞翔教授团队研发的预制手法,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都在深圳完成,每个构件根据40尺集装箱的内部空间尺寸以及操作需要来设计。为了最大化现场施工的效率以及平衡海运的费用,设计采用了折叠结构,所有结构折叠后装进五个货柜,转运至施工现场后,在一台吊机的帮助下将折叠结构打开并立体化拼塑。设计团队对施工过程非常缜密的设计和推演,确保工程上不会出较大的问题,但当货物抵达肯尼亚后,还是出现了种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
首先是清关程序出了问题。由于在项目捐赠协议签订之后肯尼亚颁布了新宪法,修改了税务细则,导致建筑构件进口的税费增加数十万元。我跑了无数个政府办公室,找了许多“说话有分量”的人,开车载着他们帮我一起前往政府大楼,以致于大楼保安甚至以为我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专职司机。我在许多政要面前哭诉无端税款带来的压力,以及再不清关会带来的滞港费用,最后内罗毕负责教育的副市长握着我的手说:“我很理解你的处境,按照法律程序我们可以启动修宪的诉讼。但你若想在当下解决税务问题,最快的办法是面向社会筹款。”最终,在各方的帮助之下,我终于在海运公司收取滞纳金之前酬足了高额税款,五个货柜从海关放行。
正当我松一口气,以为一切进入正轨时,其中一辆货柜车却忽然不见了踪影。一天之后才知道,这位司机长途奔忙,终于忍不住在路边的加油站合眼睡了一宿,而代价就是所有其他货柜车、以及卸货用的吊车都得在原地待命。由于北京学校的施工现场太过拥挤,进入场地需要经过两个陡坡和一个急转弯,巨大的货柜卡车不可能同时进入场地,所以五个货柜必须依次分别到达现场实施拆柜,而这辆失踪的货柜排行第二。
找到了司机,五辆车依次进入场地,天公又下起了大雨。卡车陷入了贫民窟外沿的泥地中。工程陷入停滞,我和另一位工程师小吴为解决方案争论了一晚没有合眼。雨停之后,我们终于得以将车辆救出泥潭,结果某个不争气的司机违规操作,未将货柜锁在车辆底座上,导致卸货时货柜差点倾覆,而重达数吨的建筑结构重重地砸在一起,预制的钢材发生了重度弯曲。在人口密度极高的贫民窟,这是极为危险的事情,我差一点和这位不负责任的司机扭打起来,为此还将裤子扯出个大洞。我和吴工巡遍全城,终于在内罗毕市郊找到了一个工厂,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神通广大,用出人意料的方法帮我们修复了钢材,也把我们从火坑里捞了出来。
内罗毕的那个雨季,我几乎每日都在经历失误的焦虑、事故的重击,也偶尔得遇获救的曙光。这种上下起伏将我折磨得身心俱疲。在此期间,MCEDO北京学校的校长班尼迪克就像马路拐角的一树花,常常在不经意间给我带来一丝温情。他知道我喜欢吃一种鸡蛋饼,被当地人称作“劳力士”(Rolex)。每当我早上需要提前开工的时候,他会悄悄地找人去买一副给我。加鸡蛋的“劳力士”是奢侈的早餐,油亮的炸鸡蛋与粗糙的烫面饼之间若即若离,折成一个三角形在塑料袋里冒着热气,一副要一百先令。项目开始以来,班尼迪克至少给我买了十几次饼,但他从来没有问我要过钱。
那天上午我就着“劳力士”坐在山坡上,焦躁的心情正悄悄远去。我一边清点已经卸下的建筑材料,一边瞥见负责招工的杰克森给排队登记的贫民窟居民科普工程安全知识。排队应聘的人中有一些极为年轻的小伙子,也有妇女——大多数是学校学生的妈妈,平时在街道上卖菜。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困惑,大多数人连扳手也没有使过,更不理解我们为何要对钢结构材料做清点整理,有人甚至想把其中的一些东西顺手拎回家去。
这时队伍中的一位妈妈因为太过好奇,径直走向堆放在不远处、垒在一起高达三米的钢结构楼板。她戴着深蓝色的传统头巾,丰腴的身材和平缓的步伐给人一种慈祥安定的感觉,然而她停在建筑材料跟前,抬头看着这堆庞大的建材,伸到一半的右手犹豫又胆怯地停在半空中,好像一只还没有学会爬树的猎豹端详着树上的同伴,好奇、渴望、又有些惊慌。校长班尼迪克不知何时出现,走到她的身边,拉起她的手放在了建材的其中一根方钢上。这位妈妈小心地松开手抚摸着钢材上下打量,又看看班尼迪克,许久后终于问出一句话:“这……这就是了吗?”没有半秒的犹豫,班尼迪克充满信心地回答:“是的,这就是孩子们的教室。”
那一刻,耀眼的阳光照在白色的钢材上,映衬出两人灿烂的笑。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盈,此前流下的汗水和泪水都已经随着赤道的日光蒸腾,烟消云散。

⬆ 作者在肯尼亚MCEDO北京学校项目中工作

⬆ 作者在马萨雷谷项目工作

⬆ 蒙巴萨“老城”街景

⬆ 蒙巴萨海边的渔民
老城里的康教授
2022年4月的一天下午,天气闷热。我浑身淌着汗,举着手机,在蒙巴萨“老城”的小巷里走着。我手机镜头里是蒙巴萨“老城”中富有斯瓦西里文化特色、蜿蜒舒适的街道,我身前不远处是蒙巴萨技术大学的康·卡兰德教授,他正激情澎湃地讲述着老城街道的历史。我手机的4G信号将我眼前的一切送往视频会议另一端——位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以及几位位于世界各地的专家面前。蒙巴萨“老城”是东非印度洋海岸线数个斯瓦西里海港城市之一。这些源自古代的城邦留下了极具特色的建成遗产——白色的石头建筑围合出蜿蜒的街道,俗称“石头城”,其中一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纳入世界遗产名录。2021年开始,同济大学和蒙巴萨技术大学展开合作,对蒙巴萨“老城”的建筑遗产进行研究。因为疫情,上海的师生和受邀的外国专家都没能来到课题研究的基地,因此我和康教授一起计划了这次“云参观”,把基地的走访搬到了线上。
4月的北半球正从寒冬中走出,而我和康教授在赤道的印度洋边挥洒着汗水。好在“老城”的街道有一种神奇的降温作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海风的咸味,小巷里走出来的风让我们体会到阵阵清凉。康教授说,蜿蜒的小巷是斯瓦西里城市天然的游击战场。数百年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征服者乘着印度洋上的季风来到这里,试图拿下蒙巴萨。这里和我去过的其他非洲城市都很不一样,漫长的历史使得蒙巴萨老城的居民拥有一种独特的沉着气质。我在不久前路过一个木工作坊,两位木匠正在做雕刻练习,他们举起一块长约两米的实木茶几。木料颜色很深,上有大大小小的孔洞。我上前询问木材的来源,木匠笑着说:“这块木头可能比你爷爷的爷爷年纪还要大。它应该是几百年前从印度洋的另一头漂洋而来。我们这里这样的木头很多,这一块曾经是船板,后来成为门,再后来成为家具,现在保养一下,可以用来做一个新的家具。”
一块木材是如何在几百年前穿越印度洋,从印度来到东非的?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在蒙巴萨斯瓦西里文化中心的图书馆开始了阅读。我读到印度洋的季风洋流,在这半年内是顺时针流动,在那半年又是逆时针的。在蒸汽动力船只发明之前的数个世纪,正是这一套洋流造就了印度洋上的贸易循环。一本英文书中说,四月从蒙巴萨下海,三周之后就可以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后来我在《星槎胜览》中也读到,郑和团队从“锡兰山”出发,三周之后就到达了东非。中世纪印度洋的贸易帝国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蒙巴萨的建成遗产也因此活了起来。
康教授对我说,蒙巴萨的历史远比印度洋的贸易更悠长、更复杂。自中世纪开始,全球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在蒙巴萨展开博弈。阿曼人来了以后是达伽马和他的葡萄牙侵略者,而后是英国殖民者。而康教授的祖先是来自伊朗地区的俾路支人,他们也曾是蒙巴萨抗击侵略者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支力量。听康教授讲述着这些历史,我不禁好奇地问:“那你觉得自己究竟是肯尼亚人、斯瓦西里人、还是俾路支人?”康教授哈哈大笑:“这怎么能是个单选题呢?我既是肯尼亚人、又是斯瓦西里人和俾路支人,我还是土生土长的蒙巴萨老城人。谁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种文化认同呢?”这时我面前的康教授变成了一副立体主义的肖像画——复杂多面而又饱含深意。一个人的确可以是立体而多面的,一座城市、一个地方也可以。
我突然想起十一年前的七月,一无所知的我经历长途飞行终于第一次降落在内罗毕国际机场。当时已是半夜十点多,接我的司机是一位热情的小伙,他不顾我困倦的表情,一边开车一边指着窗外大声说:“你看呀,这里是国家公园!长颈鹿在这里奔跑!这里是辉煌的CBD!你可以看到总统的护卫队。那边是印度人居住的地方、有特别好吃的咖喱饭!那边是联合国,这一带环境优雅,你一定会喜欢的!”此时的窗外漆黑一片,我却已然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多面和立体。我也从司机闪闪发光的眼神里感觉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向我奔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