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伟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图片提供|刘伟才
导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以自身发展为基础,不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在对非贸易和对非直接投资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部分非洲国家也审视自身,积极响应中国需求,利用中国投资,在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对于中非之间的这种密切互动,欧美学界一度颇多负面评价和臆测,刻意忽视中国之于非洲发展的积极意义或对种种积极意义认识不清。究其原因,除了部分论者的别有用心外,主要还是基于切实数据和具体案例的研究不够。
阿亚柳·马莫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生产性投资与工业化》选取埃塞俄比亚为国别对象,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推动埃轻工部门发展的力量和机制进行了探讨,比较中肯地阐明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之于非洲国家制造业尤其是轻工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为非洲国家对中国投资的利用和中国对非投资的实施提供了一些参考。
埃塞俄比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进入快速经济增长轨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和出口方面的地位日益突出,这对那些希望提升制造业能力的非洲国家构成强大的吸引力。埃政府的产业政策强调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重视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落实工业发展战略,尤其是吸引来自中国的制造业投资。
中国的直接投资如何推动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化?阿亚柳·马莫从皮革业和纺织品服装业入手,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
首先是埃塞俄比亚方面的相关政策及其影响。马莫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工业与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将经济转型与高速增长置于发展战略核心位置;第二,将发展制造业和推动工业化作为实现转型的关键路径;第三,将轻工业作为优先发展领域,以强化与农业的产业关联,提升出口,创造就业,并加速知识与技术转移。埃政府采取了以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制造业、重点支持能够促进出口与技术转移的中大型企业的政策取向,并在投资政策与制度体系上进行改革,明确瞄准重点产业、重点地区与重点企业。
其次是埃塞俄比亚相关机构的协调行动。埃政府在精心选定的中国相关省份举办投资推介会,投资推介面向的也是具有规模效应、深度参与出口并由较强价值链纵向整合能力的企业。在具体的投资推介活动中,埃重视安排包括总理在内的各路高官出席,以为中国投资企业提供信心。与此同时,埃投资管理机构亦保持持续的联络与平台支持。事实证明,这些企业在促进就业、扩大出口方面贡献明显,在工人技能培养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一些企业在管理与技术能力本地化方面表现突出,一些企业在垂直一体化方面业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在诸多具体举措中,建立和发展工业园区是一个关键。2010年埃塞俄比亚仅有一个工业园,而在实施新战略后,至2021年,政府与私人开发商共新建了24个工业园。其中,东部工业园、上海制鞋城、南阳皮革与制鞋园、莫乔皮革城、阿雷尔蒂建筑材料产业园等由中国开发商建设。除了注重依托中国力量发展工业园区外,埃政府还学习中国经验,同时也不忘吸收了新加坡、韩国、越南等国的经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重要支撑。埃政府优先安排由中国优惠贷款和商业贷款支持的项目,并将重点放在服务制造业和出口领域,兴建了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公路网、水电站、风力发电场和输电线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
再次是中国投资的效应。数据资料表明,进入埃塞俄比亚的中国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规模竞争力、资本实力、管理与技术能力,能够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运作,而无需依赖本地银行体系融资,从而避免对本地企业造成挤压效应。这些企业普遍引进新设备、投入大量资本和人力资源,并重视工业劳动力培训。以此为基础,中国投资推动了埃塞俄比亚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扩张,创造了制造业就业岗位,带动了货物出口增长与资本形成,对埃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具有显著贡献。
但是,仍有若干不均衡和不足存在。这些不均衡和不足包括:中国投资对纺织品服装业的促进效果显著优于皮革业;纳入工业园管理体系的中国投资企业有加强的绩效提升能力并能在更好地适应埃工业化战略目标,但园区外企业较难实现同样效果;中国投资企业总体上对工人技能提升与生产技术知识传授有积极贡献,但与当地企业的产业关联与价值增值联系往往不足,合资机制与本地管理能力建设也不到位;工业园战略带来的政策学习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绩效,但其他政策领域仍存在约束,财政与海关管理、外汇短缺、物流成本高与发展缓慢以及跨行业政策一致性不佳等因素仍是制约。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马莫就工业政策的设计实施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提出了若干见解。首先,稳健而持续的经贸关系是根本。中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经贸关系在过去二十年中不断加强并持续发展,被视作中非合作的积极典范之一。双方关系的深化通过多重渠道逐步推进,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与中非合作论坛日益强调工业化转型的取向与埃塞俄比亚政府逐步推进的工业化战略形成了较好的适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互为对方提供了机遇。
但其次要明确的是,机遇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有效的发展。即便埃塞俄比亚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表现出较多的主动性,但相关效果仍有未尽之处。如果跳出埃塞俄比亚,更是会发现,尽管2000年后中非合作迅速扩展,却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采取了同样有效的战略,战略主动性、政策自主性与执行能力的差异使得中国直接投资在不同国家产生的效果出现参差。
再次,工业政策与外资管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张力,需要不断调整以应对新挑战,这是一个充满博弈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以皮革业为例,马莫认为,尽管埃塞俄比亚拥有丰富的畜牧资源,但原皮短缺与皮革质量问题限制了后向关联的发展与全产业链垂直整合;政府政策在推动产业增值和出口结构改善方面长期缺乏有效性,使皮革业陷入低资本化与低生产率的路径依赖,难以升级;一些企业抵制政府推动的成品出口政策,继续专注于低增值、低风险的皮革初加工,导致外国直接投资无法构建显著的额外优势。
此外,中国投资面临的挑战也比较突出。大多数企业面临税务管理体系不健全、物流成本高、外汇短缺以及劳工法与劳工管理相关障碍。工业园区开发商与大型企业还遭遇土地与公共设施供给延迟、联邦与地方政府间协调不足等问题。埃塞俄比亚显在和潜在的政治动荡乃至冲突风险也会对投资者信心造成重大冲击。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是以埃塞俄比亚为案例,并且只聚焦皮革业和纺织品服装业这两个行业,但相关结论仍有一定的普遍性价值。对于广大非洲国家来说,基于自身条件和需求制定并实施合理的经济政策,营造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以此吸引并保持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进而构建产业链纵向整合及与农业的生产联动,培育有活力的本土企业,是一条应长期遵循的路径。对于中国来说,在意识到对非投资机遇的同时保持对在非洲风险的警惕,根据不同非洲国家的不同情况实施差异化投资,亦是一项需要不断揣摩并在实践中磨合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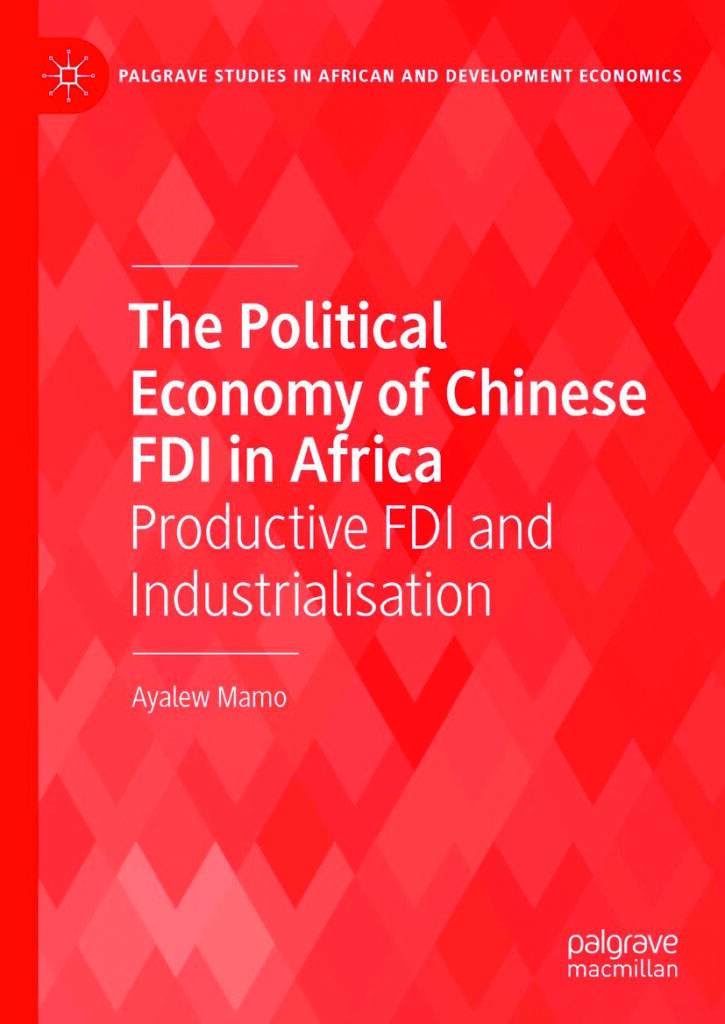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Ayalew Mam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DI in Africa: Productive FDI and Industrialis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4. |
作者简介:
阿亚柳·马莫(Ayalew Mamo),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录
1.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DI in Africa
2. Industrial Policy, the State, and Late Industrialisation in Africa
3. Dynamics and Evolution of China—Africa Economic Ties
4. Chinese FDI in Ethiopian Textile Industry: A Dynamic Model
5. Chinese FDI in Ethiopian Leather Industry: Mixed Outcomes
6.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FDI in African Manufacturing
7. Chinese Outward Manufacturing FDI in Africa: Performance, Policy Challenges, and Lessons

